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
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
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fāngtāo) 通讯员 马磊
接上(shàng)篇:良渚日,再深入一点:寻找董聿茂(上)
从水路过陆路,步步转运,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hōngzhà),1940年底,西湖博物馆又转移(zhuǎnyí)到了丽水三岩寺。
董聿茂是奉化人,他(tā)知道奉化已经沦陷,叫来同村(tóngcūn)老乡康美业,让他负责管理标本,同时跟着冯谋鸿先生学习采集制作动物标本。
那年(nànián)康美业(kāngměiyè)18岁。董聿茂(dǒngyùmào)反复叮嘱他要勤俭创业,物尽其用,每次制作昆虫(kūnchóng)标本,总是算好所需昆虫针的枚数,定量发给大家,不允许随意浪费。董聿茂发给康美业一把解剖刀,他用了再磨,磨了再用,直到1977年退休。
博物馆除了展出工作停办外,采集、制作标本和资源调查等日常工作,依然有序(yǒuxù)进行。大家(dàjiā)学习采集蝴蝶标本,自己做猎枪子弹(zǐdàn),有条件时(shí)就把带来的标本材料临时展出。董聿茂还给大家上动物学课程,鼓励年轻人多读书,指定了阅读(yuèdú)书目,还要定期考试。康美业不敢偷懒,这为他日后的博物馆工作打下了基础。
逃难没有目的地,1941年,大部队又辗转到了松阳南洲村(nánzhōucūn)。
“C位就是董(dǒng)伯伯。”马磊指了指博物馆迁徙松阳时的(de)职员合影,如今挂在自博办公区的文化墙上。
 C位董聿茂,右一钱惠馨,左四钟国仪,右四钟钱伉俪的二(èr)儿子
1939年(nián)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董聿茂同时还兼着(zhe)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他要搭(dā)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往返一次需时(xūshí)三天。
此时(cǐshí),爸爸骑(qí)一辆自行车,一大早从龙泉出发,骑十几里路,到松阳南洲村时已是下午。董振一说,有次刹车(shāchē)坏了,爸爸摔了一跤,又继续骑。
1941年夏天,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动身那天,家人和随行物品(wùpǐn)都上船了,8岁的董振一也在船上,但是(dànshì),爸爸不放心博物馆(bówùguǎn)人员和标本物品,又跑回了馆里。
他刚到(dào)馆里,康美业就听到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旁的一个山洞跑去。进洞后不久,头顶响起了阵阵(zhènzhèn)轰炸声,从洞中望去,山石(shānshí)崩落,尘土飞扬。约一刻钟后,洞外没了声响。
穿过火海,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许多船已(yǐ)被(bèi)炸。一条船上,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董聿茂上前探问,给(gěi)他一些钱,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治伤。
在溪对面的大树下,他(tā)终于看到了夫人和(hé)孩子,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那里有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shūgǎo)。
康美业回忆,找到了,那只船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船上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其余(qíyú)皆散落(sànluò)水中。
“他(tā)当时那种怅然的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nàyàng)的神情。”康美业这样写道。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bāngmáng)打捞残留书稿,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wénshū)赠送给了康美业。
然而,1941年7月,教育厅却下令停办(tíngbàn)西湖博物馆,遣散所有人员,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让董聿茂(dǒngyùmào)把全部馆产交给“松阳县民众教育馆”接收(jiēshōu)。
丽水已经(yǐjīng)沦陷,松阳也许很快失守。董聿茂知道,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mínjiàoguǎn)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
康美业记得,明明自身难保(zìshēnnánbǎo),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如何安排我们这些(zhèxiē)“失业”的人,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hǎobùróngyì)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
许多单身汉领了(lǐngle)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后自谋生路去了,康美业(měiyè)的父辈与(yǔ)董老为故交,奉化已沦陷,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
在康美业的描述里,此时,董聿茂“又作出了一个(yígè)惊人(rén)的决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自费承担收藏馆内所有藏品、标本和图书资料,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děng)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xiànchéng)。
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都留下了(le)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过去,我们用“斗士”来形容拼命保护文物遗产的(de)毛昭晰,然而1997年,在董聿茂先生诞辰(dànchén)100周年纪念会上,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董伯伯真是一位(yīwèi)了不起(liǎobùqǐ)的人物,他是优秀的学者,也是正义的斗士。”
此时,同样是奉化人,毛昭晰全家也避难(bìnàn)也到了龙泉。
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进犯(jìnfàn)浙东,金华、丽水相继失守,龙泉也很危险(wēixiǎn)。
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在(zài)这年6、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到9月间,日寇(rìkòu)从丽水撤退,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而浙大龙泉分校仍(réng)在福建松溪。
为了不让毛昭晰辍学,毛路真让他一个(yígè)人从松溪返回龙泉(lóngquán)读书,嘱咐他,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
毛昭晰13岁(suì),背了(le)一个小包袱,穿了一双草鞋走了四天,找到了董伯伯。
董聿茂为了(le)疏散和保护西湖博物馆的藏品,坚持(jiānchí)不离开龙泉。看到毛昭晰,热情接待,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
董伯伯租住的民房在龙泉(lóngquán)县城(xiànchéng)的水南,有七、八间房子,大多堆着木箱。毛昭晰知道,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标本和图书仪器,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què)很挤。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长着一些杂树。每天一早,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和(hé)古文。晚上,董(dǒng)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
董振一说,爸爸虽(suī)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但(dàn)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为了维持生活,爸爸又自费租(zū)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种蔬菜,他跟在爸爸后面帮忙拔草,妈妈养了一头(yītóu)猪。爸爸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租民房,把图书标本、历史文物保存起来。
同时,董聿茂(dǒngyùmào)又把钟国仪和顾剑谊介绍(jièshào)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韦植说(shuō),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好在他朋友多,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管仓库,在粮站拿工资,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shēngjì)问题。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chūqùwán)。董振一说,除了打猎。
马磊(mǎlěi)1997年进单位,馆里还有6把猎枪,当时做标本都(dōu)是馆员自己去采集。
爸爸枪法很准,尤其打老鹰,“百发百中(bǎifābǎizhòng)”,他教大家,射击要略偏老鹰前面一点,子弹飞行(fēixíng)还有一段距离,这样才能一枪命中。
毛昭晰还(hái)小,跟在康美业后面叫,美业哥哥,给我打一枪。
C位董聿茂,右一钱惠馨,左四钟国仪,右四钟钱伉俪的二(èr)儿子
1939年(nián)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董聿茂同时还兼着(zhe)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他要搭(dā)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往返一次需时(xūshí)三天。
此时(cǐshí),爸爸骑(qí)一辆自行车,一大早从龙泉出发,骑十几里路,到松阳南洲村时已是下午。董振一说,有次刹车(shāchē)坏了,爸爸摔了一跤,又继续骑。
1941年夏天,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动身那天,家人和随行物品(wùpǐn)都上船了,8岁的董振一也在船上,但是(dànshì),爸爸不放心博物馆(bówùguǎn)人员和标本物品,又跑回了馆里。
他刚到(dào)馆里,康美业就听到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旁的一个山洞跑去。进洞后不久,头顶响起了阵阵(zhènzhèn)轰炸声,从洞中望去,山石(shānshí)崩落,尘土飞扬。约一刻钟后,洞外没了声响。
穿过火海,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许多船已(yǐ)被(bèi)炸。一条船上,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董聿茂上前探问,给(gěi)他一些钱,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治伤。
在溪对面的大树下,他(tā)终于看到了夫人和(hé)孩子,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那里有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shūgǎo)。
康美业回忆,找到了,那只船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船上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其余(qíyú)皆散落(sànluò)水中。
“他(tā)当时那种怅然的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nàyàng)的神情。”康美业这样写道。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bāngmáng)打捞残留书稿,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wénshū)赠送给了康美业。
然而,1941年7月,教育厅却下令停办(tíngbàn)西湖博物馆,遣散所有人员,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让董聿茂(dǒngyùmào)把全部馆产交给“松阳县民众教育馆”接收(jiēshōu)。
丽水已经(yǐjīng)沦陷,松阳也许很快失守。董聿茂知道,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mínjiàoguǎn)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
康美业记得,明明自身难保(zìshēnnánbǎo),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如何安排我们这些(zhèxiē)“失业”的人,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hǎobùróngyì)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
许多单身汉领了(lǐngle)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后自谋生路去了,康美业(měiyè)的父辈与(yǔ)董老为故交,奉化已沦陷,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
在康美业的描述里,此时,董聿茂“又作出了一个(yígè)惊人(rén)的决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自费承担收藏馆内所有藏品、标本和图书资料,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děng)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xiànchéng)。
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都留下了(le)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过去,我们用“斗士”来形容拼命保护文物遗产的(de)毛昭晰,然而1997年,在董聿茂先生诞辰(dànchén)100周年纪念会上,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董伯伯真是一位(yīwèi)了不起(liǎobùqǐ)的人物,他是优秀的学者,也是正义的斗士。”
此时,同样是奉化人,毛昭晰全家也避难(bìnàn)也到了龙泉。
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进犯(jìnfàn)浙东,金华、丽水相继失守,龙泉也很危险(wēixiǎn)。
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在(zài)这年6、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到9月间,日寇(rìkòu)从丽水撤退,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而浙大龙泉分校仍(réng)在福建松溪。
为了不让毛昭晰辍学,毛路真让他一个(yígè)人从松溪返回龙泉(lóngquán)读书,嘱咐他,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
毛昭晰13岁(suì),背了(le)一个小包袱,穿了一双草鞋走了四天,找到了董伯伯。
董聿茂为了(le)疏散和保护西湖博物馆的藏品,坚持(jiānchí)不离开龙泉。看到毛昭晰,热情接待,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
董伯伯租住的民房在龙泉(lóngquán)县城(xiànchéng)的水南,有七、八间房子,大多堆着木箱。毛昭晰知道,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标本和图书仪器,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què)很挤。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长着一些杂树。每天一早,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和(hé)古文。晚上,董(dǒng)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
董振一说,爸爸虽(suī)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但(dàn)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为了维持生活,爸爸又自费租(zū)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种蔬菜,他跟在爸爸后面帮忙拔草,妈妈养了一头(yītóu)猪。爸爸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租民房,把图书标本、历史文物保存起来。
同时,董聿茂(dǒngyùmào)又把钟国仪和顾剑谊介绍(jièshào)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韦植说(shuō),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好在他朋友多,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管仓库,在粮站拿工资,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shēngjì)问题。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chūqùwán)。董振一说,除了打猎。
马磊(mǎlěi)1997年进单位,馆里还有6把猎枪,当时做标本都(dōu)是馆员自己去采集。
爸爸枪法很准,尤其打老鹰,“百发百中(bǎifābǎizhòng)”,他教大家,射击要略偏老鹰前面一点,子弹飞行(fēixíng)还有一段距离,这样才能一枪命中。
毛昭晰还(hái)小,跟在康美业后面叫,美业哥哥,给我打一枪。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今年92岁,坚持要来院里接受(jiēshòu)采访
抗战中还有一件(yījiàn)事,也被不同的人提起。
姜乃澄执笔的《董聿茂教授传略》一文中讲到,日寇占领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bówùguǎn)后,在南京成立了“中支建设(jiànshè)资料整理事务所”,接管沪杭各地(gèdì)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在杭州建有“杭州出张所”(注:日语出张所,即办事处)。1942年,日本(rìběn)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曾(céng)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gōngzuò),被董聿茂断然拒绝。
韦植1951年(nián)到西湖博物馆工作,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做库藏。对于这一段故事,他有另一番回忆:“日寇占领杭州后,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zhěnglǐ)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负责人恰好(qiàhǎo)是先生(xiānshēng)留日的同学,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先生虽挂念博物馆,但昔年(xīnián)同学已在敌国,焉能失辱民族大节,乃凛然回绝,一直(yìzhí)留在龙泉坚持(jiānchí)至抗战胜利。”
细节略有(yǒu)不同(bùtóng)。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曾有一个强烈(qiángliè)的感受,从上帝视角俯瞰、全局回顾的历史和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shì)不同的,对同一真实事件(shìjiàn)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存在差异,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需要保留。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教育厅知道(zhīdào)西湖博物馆的财产(cáichǎn)保存完好,又下令在龙泉恢复办馆。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以抗议教育厅(jiàoyùtīng)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自然标本(biāoběn)和图书仪器。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被炸损失外,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déyǐ)完好(wánhǎo)保存,直至今天。
《浙江通志》有一条数据: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馆藏(guǎncáng)自然(zìrán)类标本达11289件。
1945年夏天(xiàtiān),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史地系。8月,日寇投降(tóuxiáng),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
董聿茂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zhǔrèn)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zhízhì)1952年2月。
当时浙大(zhèdà)有一条制度(zhìdù),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一些文科(wénkē)的课程,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用(yòng)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每周上课三小时,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tiáolǐqīngxī),重点突出,使人很感兴趣。”
考研究生时,他选择了与生物学(shēngwùxué)密切相关的(de)“人类学”,“这和董伯伯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51年,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找他(tā)。此时,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guǎnzhǎng)。
董聿茂想到(xiǎngdào)毛昭晰(máozhāoxī)读的人类学专业所包含的学科如体质人类学、化石(huàshí)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
毛昭晰的理想(lǐxiǎng)是当教师,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
但,我们都知道了后来的(de)事。
“人生真是奇妙。当年董伯伯(bóbó)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我没有去。三十多年之后,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董伯伯开心地笑了,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nàgè)地方。”他在《怀念董聿茂(dǒngyùmào)教授》中这样写道。
董聿茂对毛昭晰说,他希望(xīwàng)浙江(zhèjiāng)省的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博物馆,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
后来,毛昭晰又对更(gèng)多后辈说过同样的话:“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xuéxiào)。”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
董聿茂(dǒngyùmào)一直叫韦植“小韦”,从22岁进西湖博物馆,一直叫到小韦退休(tuìxiū)。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21周年合影,韦植帮我们认人(rén):董聿茂、钟国仪、钱惠馨、康美业、何天行(hétiānxíng)(时任历史部主任)……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今年92岁,坚持要来院里接受(jiēshòu)采访
抗战中还有一件(yījiàn)事,也被不同的人提起。
姜乃澄执笔的《董聿茂教授传略》一文中讲到,日寇占领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bówùguǎn)后,在南京成立了“中支建设(jiànshè)资料整理事务所”,接管沪杭各地(gèdì)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在杭州建有“杭州出张所”(注:日语出张所,即办事处)。1942年,日本(rìběn)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曾(céng)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gōngzuò),被董聿茂断然拒绝。
韦植1951年(nián)到西湖博物馆工作,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做库藏。对于这一段故事,他有另一番回忆:“日寇占领杭州后,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zhěnglǐ)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负责人恰好(qiàhǎo)是先生(xiānshēng)留日的同学,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先生虽挂念博物馆,但昔年(xīnián)同学已在敌国,焉能失辱民族大节,乃凛然回绝,一直(yìzhí)留在龙泉坚持(jiānchí)至抗战胜利。”
细节略有(yǒu)不同(bùtóng)。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曾有一个强烈(qiángliè)的感受,从上帝视角俯瞰、全局回顾的历史和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shì)不同的,对同一真实事件(shìjiàn)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存在差异,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需要保留。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教育厅知道(zhīdào)西湖博物馆的财产(cáichǎn)保存完好,又下令在龙泉恢复办馆。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以抗议教育厅(jiàoyùtīng)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自然标本(biāoběn)和图书仪器。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被炸损失外,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déyǐ)完好(wánhǎo)保存,直至今天。
《浙江通志》有一条数据: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馆藏(guǎncáng)自然(zìrán)类标本达11289件。
1945年夏天(xiàtiān),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史地系。8月,日寇投降(tóuxiáng),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
董聿茂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zhǔrèn)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zhízhì)1952年2月。
当时浙大(zhèdà)有一条制度(zhìdù),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一些文科(wénkē)的课程,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用(yòng)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每周上课三小时,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tiáolǐqīngxī),重点突出,使人很感兴趣。”
考研究生时,他选择了与生物学(shēngwùxué)密切相关的(de)“人类学”,“这和董伯伯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51年,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找他(tā)。此时,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guǎnzhǎng)。
董聿茂想到(xiǎngdào)毛昭晰(máozhāoxī)读的人类学专业所包含的学科如体质人类学、化石(huàshí)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
毛昭晰的理想(lǐxiǎng)是当教师,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
但,我们都知道了后来的(de)事。
“人生真是奇妙。当年董伯伯(bóbó)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我没有去。三十多年之后,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董伯伯开心地笑了,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nàgè)地方。”他在《怀念董聿茂(dǒngyùmào)教授》中这样写道。
董聿茂对毛昭晰说,他希望(xīwàng)浙江(zhèjiāng)省的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博物馆,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
后来,毛昭晰又对更(gèng)多后辈说过同样的话:“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xuéxiào)。”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
董聿茂(dǒngyùmào)一直叫韦植“小韦”,从22岁进西湖博物馆,一直叫到小韦退休(tuìxiū)。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21周年合影,韦植帮我们认人(rén):董聿茂、钟国仪、钱惠馨、康美业、何天行(hétiānxíng)(时任历史部主任)……
 那年,韦植从安徽大学农学院(nóngxuéyuàn)森林系毕业,堂兄弟“大韦”韦思奇,杭大农学院毕业,有两个(liǎnggè)选择,一是去南京大学,跟着(gēnzhe)小麦专家金善宝,做他的助教,二是去西湖博物馆,听说董馆长要人。
1951年,大韦拉着小韦,你陪(péi)我去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职员家属都住(zhù)在(zài)院里,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院子里种满菜。
大韦说,这个地方好,可以安家(ānjiā)。
董(dǒng)馆长很高兴,希望大韦来这里工作。
还有这一位呢?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xiǎowéi)。
小韦说,我(wǒ)现在还没有定。如果没有工作,我准备去丽水(líshuǐ)林业学校教书。
你不要去了(le),你也到(dào)博物馆里来吧。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你们去教育厅报到吧。
第二天,大韦上午报到,小韦(xiǎowéi)下午报到。
“先生常说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学术研究(xuéshùyánjiū)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自己(zìjǐ)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biérén)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
一次,浙师院师生去舟山(zhōushān)野外实习(shíxí),董聿茂和韦植同去。董先生在海边指导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在泥涂中只能赤脚,叮嘱必须(bìxū)掌握涨潮时刻,及时上岸。
回来,大家都很疲惫,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又继续指导大家如何(rúhé)处埋(mái)标本,如何作好记录等等。韦植第一次(dìyīcì)才明白,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先生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不准(bùzhǔn)马虎。“
标本采回(cǎihuí)馆,也没有结束,董聿茂还要办汇报展览,就是在工作室内把标本摊开,让全馆同事来(lái)参观、评议和检查。“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de)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
1953年,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更名为浙江博物馆。“小韦啊,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bàn)起来的。”董聿茂说,两个馆并在一起,一个是人文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办不好(bùhǎo)的。
1984年7月,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单独建制,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韦植是独立(dúlì)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但是馆里还没(méi)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玻璃瓶(bōlípíng)标本没地方摆,只能放在屋檐下。
韦植记忆中,1987年冬天下大雪,下了(le)一晚上,好多药水泡的鱼类(yúlèi)标本、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
“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这个事情我(wǒ)不敢告诉他,他会伤心的。”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对方说,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一挤(yījǐ)好了。
“文物(wénwù)和标本这两类,不能(bùnéng)摆在一起,标本都是酒精、福尔马林。文物库房的标本,用的是樟脑丸、樟脑粉,万一有个(yǒugè)火灾,文物就会毁掉。”韦植不同意。
1988年(nián),标本楼批下来了,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
标本楼建成,韦植去家里(jiālǐ)看董聿茂。他发烧很多天了。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突然来了劲头,“有了标本楼,你们要(yào)好好干,不同(bùtóng)的标本要分类,仪器、图书和标本要分开……”
小韦当时想,已经不当馆长了,你操这个(zhègè)心干啥?
2个月后,1990年1月12日(rì),董聿茂去世。
“董馆长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de)事业(shìyè),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的。”多年之后,韦植完全理解了董聿茂。
1987年春天,杭州大学(hángzhōudàxué)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dào)西湖风景区春游,董聿茂和毛昭晰都在其中,那年,董聿茂90岁,年龄最大。在玉皇山顶的(de)饭店吃午饭的时候(shíhòu),年纪最小的毛昭晰,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
他毫无准备,抬起头,董伯伯(bóbó)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jiǔshí)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yīyàng)的健康长寿。”
马磊发来一条微信:“人的(de)生命分很多种,博物馆也是董馆长的孩子,永远(yǒngyuǎn)活着。”
1986年6月2日,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zhǔrèn)方行、上海博物馆(shànghǎibówùguǎn)馆长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良渚(liángzhǔ)反山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gōngdì)。
阿达,你不要动(dòng)哦。毛昭晰对发掘领队王明达说。
什么不要动?王明达问(wèn)。
为了(wèile)确证所发现的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牟永抗(móuyǒngkàng)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露出(lùchū)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确定了!确定了!”王明达大嗓子一喊,大家(dàjiā)围在墓坑边(biān),除了玉琮外,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王明达(wángmíngdá)日记:
6月10日(rì),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 日,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bǎo)等(děng)视察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
本来的补贴——给浙江(zhèjiāng)小百花越剧团10万、浙江越剧团10万,李德葆拍板,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kǎogǔsuǒ)。
那时,毛昭晰告诉他(tā)的董伯伯了吗?
(感谢陈水华、马磊、王卫东、彭亚君(péngyàjūn)、方一锋、吴庐春(chūn)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那年,韦植从安徽大学农学院(nóngxuéyuàn)森林系毕业,堂兄弟“大韦”韦思奇,杭大农学院毕业,有两个(liǎnggè)选择,一是去南京大学,跟着(gēnzhe)小麦专家金善宝,做他的助教,二是去西湖博物馆,听说董馆长要人。
1951年,大韦拉着小韦,你陪(péi)我去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职员家属都住(zhù)在(zài)院里,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院子里种满菜。
大韦说,这个地方好,可以安家(ānjiā)。
董(dǒng)馆长很高兴,希望大韦来这里工作。
还有这一位呢?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xiǎowéi)。
小韦说,我(wǒ)现在还没有定。如果没有工作,我准备去丽水(líshuǐ)林业学校教书。
你不要去了(le),你也到(dào)博物馆里来吧。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你们去教育厅报到吧。
第二天,大韦上午报到,小韦(xiǎowéi)下午报到。
“先生常说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学术研究(xuéshùyánjiū)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自己(zìjǐ)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biérén)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
一次,浙师院师生去舟山(zhōushān)野外实习(shíxí),董聿茂和韦植同去。董先生在海边指导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在泥涂中只能赤脚,叮嘱必须(bìxū)掌握涨潮时刻,及时上岸。
回来,大家都很疲惫,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又继续指导大家如何(rúhé)处埋(mái)标本,如何作好记录等等。韦植第一次(dìyīcì)才明白,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先生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不准(bùzhǔn)马虎。“
标本采回(cǎihuí)馆,也没有结束,董聿茂还要办汇报展览,就是在工作室内把标本摊开,让全馆同事来(lái)参观、评议和检查。“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de)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
1953年,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更名为浙江博物馆。“小韦啊,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bàn)起来的。”董聿茂说,两个馆并在一起,一个是人文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办不好(bùhǎo)的。
1984年7月,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单独建制,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韦植是独立(dúlì)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但是馆里还没(méi)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玻璃瓶(bōlípíng)标本没地方摆,只能放在屋檐下。
韦植记忆中,1987年冬天下大雪,下了(le)一晚上,好多药水泡的鱼类(yúlèi)标本、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
“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这个事情我(wǒ)不敢告诉他,他会伤心的。”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对方说,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一挤(yījǐ)好了。
“文物(wénwù)和标本这两类,不能(bùnéng)摆在一起,标本都是酒精、福尔马林。文物库房的标本,用的是樟脑丸、樟脑粉,万一有个(yǒugè)火灾,文物就会毁掉。”韦植不同意。
1988年(nián),标本楼批下来了,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
标本楼建成,韦植去家里(jiālǐ)看董聿茂。他发烧很多天了。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突然来了劲头,“有了标本楼,你们要(yào)好好干,不同(bùtóng)的标本要分类,仪器、图书和标本要分开……”
小韦当时想,已经不当馆长了,你操这个(zhègè)心干啥?
2个月后,1990年1月12日(rì),董聿茂去世。
“董馆长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de)事业(shìyè),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的。”多年之后,韦植完全理解了董聿茂。
1987年春天,杭州大学(hángzhōudàxué)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dào)西湖风景区春游,董聿茂和毛昭晰都在其中,那年,董聿茂90岁,年龄最大。在玉皇山顶的(de)饭店吃午饭的时候(shíhòu),年纪最小的毛昭晰,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
他毫无准备,抬起头,董伯伯(bóbó)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jiǔshí)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yīyàng)的健康长寿。”
马磊发来一条微信:“人的(de)生命分很多种,博物馆也是董馆长的孩子,永远(yǒngyuǎn)活着。”
1986年6月2日,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zhǔrèn)方行、上海博物馆(shànghǎibówùguǎn)馆长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良渚(liángzhǔ)反山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gōngdì)。
阿达,你不要动(dòng)哦。毛昭晰对发掘领队王明达说。
什么不要动?王明达问(wèn)。
为了(wèile)确证所发现的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牟永抗(móuyǒngkàng)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露出(lùchū)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确定了!确定了!”王明达大嗓子一喊,大家(dàjiā)围在墓坑边(biān),除了玉琮外,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王明达(wángmíngdá)日记:
6月10日(rì),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 日,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bǎo)等(děng)视察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
本来的补贴——给浙江(zhèjiāng)小百花越剧团10万、浙江越剧团10万,李德葆拍板,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kǎogǔsuǒ)。
那时,毛昭晰告诉他(tā)的董伯伯了吗?
(感谢陈水华、马磊、王卫东、彭亚君(péngyàjūn)、方一锋、吴庐春(chūn)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fāngtāo) 通讯员 马磊
接上(shàng)篇:良渚日,再深入一点:寻找董聿茂(上)
从水路过陆路,步步转运,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hōngzhà),1940年底,西湖博物馆又转移(zhuǎnyí)到了丽水三岩寺。
董聿茂是奉化人,他(tā)知道奉化已经沦陷,叫来同村(tóngcūn)老乡康美业,让他负责管理标本,同时跟着冯谋鸿先生学习采集制作动物标本。
那年(nànián)康美业(kāngměiyè)18岁。董聿茂(dǒngyùmào)反复叮嘱他要勤俭创业,物尽其用,每次制作昆虫(kūnchóng)标本,总是算好所需昆虫针的枚数,定量发给大家,不允许随意浪费。董聿茂发给康美业一把解剖刀,他用了再磨,磨了再用,直到1977年退休。
博物馆除了展出工作停办外,采集、制作标本和资源调查等日常工作,依然有序(yǒuxù)进行。大家(dàjiā)学习采集蝴蝶标本,自己做猎枪子弹(zǐdàn),有条件时(shí)就把带来的标本材料临时展出。董聿茂还给大家上动物学课程,鼓励年轻人多读书,指定了阅读(yuèdú)书目,还要定期考试。康美业不敢偷懒,这为他日后的博物馆工作打下了基础。
逃难没有目的地,1941年,大部队又辗转到了松阳南洲村(nánzhōucūn)。
“C位就是董(dǒng)伯伯。”马磊指了指博物馆迁徙松阳时的(de)职员合影,如今挂在自博办公区的文化墙上。
 C位董聿茂,右一钱惠馨,左四钟国仪,右四钟钱伉俪的二(èr)儿子
1939年(nián)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董聿茂同时还兼着(zhe)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他要搭(dā)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往返一次需时(xūshí)三天。
此时(cǐshí),爸爸骑(qí)一辆自行车,一大早从龙泉出发,骑十几里路,到松阳南洲村时已是下午。董振一说,有次刹车(shāchē)坏了,爸爸摔了一跤,又继续骑。
1941年夏天,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动身那天,家人和随行物品(wùpǐn)都上船了,8岁的董振一也在船上,但是(dànshì),爸爸不放心博物馆(bówùguǎn)人员和标本物品,又跑回了馆里。
他刚到(dào)馆里,康美业就听到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旁的一个山洞跑去。进洞后不久,头顶响起了阵阵(zhènzhèn)轰炸声,从洞中望去,山石(shānshí)崩落,尘土飞扬。约一刻钟后,洞外没了声响。
穿过火海,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许多船已(yǐ)被(bèi)炸。一条船上,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董聿茂上前探问,给(gěi)他一些钱,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治伤。
在溪对面的大树下,他(tā)终于看到了夫人和(hé)孩子,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那里有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shūgǎo)。
康美业回忆,找到了,那只船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船上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其余(qíyú)皆散落(sànluò)水中。
“他(tā)当时那种怅然的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nàyàng)的神情。”康美业这样写道。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bāngmáng)打捞残留书稿,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wénshū)赠送给了康美业。
然而,1941年7月,教育厅却下令停办(tíngbàn)西湖博物馆,遣散所有人员,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让董聿茂(dǒngyùmào)把全部馆产交给“松阳县民众教育馆”接收(jiēshōu)。
丽水已经(yǐjīng)沦陷,松阳也许很快失守。董聿茂知道,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mínjiàoguǎn)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
康美业记得,明明自身难保(zìshēnnánbǎo),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如何安排我们这些(zhèxiē)“失业”的人,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hǎobùróngyì)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
许多单身汉领了(lǐngle)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后自谋生路去了,康美业(měiyè)的父辈与(yǔ)董老为故交,奉化已沦陷,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
在康美业的描述里,此时,董聿茂“又作出了一个(yígè)惊人(rén)的决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自费承担收藏馆内所有藏品、标本和图书资料,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děng)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xiànchéng)。
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都留下了(le)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过去,我们用“斗士”来形容拼命保护文物遗产的(de)毛昭晰,然而1997年,在董聿茂先生诞辰(dànchén)100周年纪念会上,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董伯伯真是一位(yīwèi)了不起(liǎobùqǐ)的人物,他是优秀的学者,也是正义的斗士。”
此时,同样是奉化人,毛昭晰全家也避难(bìnàn)也到了龙泉。
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进犯(jìnfàn)浙东,金华、丽水相继失守,龙泉也很危险(wēixiǎn)。
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在(zài)这年6、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到9月间,日寇(rìkòu)从丽水撤退,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而浙大龙泉分校仍(réng)在福建松溪。
为了不让毛昭晰辍学,毛路真让他一个(yígè)人从松溪返回龙泉(lóngquán)读书,嘱咐他,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
毛昭晰13岁(suì),背了(le)一个小包袱,穿了一双草鞋走了四天,找到了董伯伯。
董聿茂为了(le)疏散和保护西湖博物馆的藏品,坚持(jiānchí)不离开龙泉。看到毛昭晰,热情接待,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
董伯伯租住的民房在龙泉(lóngquán)县城(xiànchéng)的水南,有七、八间房子,大多堆着木箱。毛昭晰知道,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标本和图书仪器,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què)很挤。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长着一些杂树。每天一早,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和(hé)古文。晚上,董(dǒng)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
董振一说,爸爸虽(suī)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但(dàn)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为了维持生活,爸爸又自费租(zū)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种蔬菜,他跟在爸爸后面帮忙拔草,妈妈养了一头(yītóu)猪。爸爸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租民房,把图书标本、历史文物保存起来。
同时,董聿茂(dǒngyùmào)又把钟国仪和顾剑谊介绍(jièshào)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韦植说(shuō),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好在他朋友多,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管仓库,在粮站拿工资,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shēngjì)问题。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chūqùwán)。董振一说,除了打猎。
马磊(mǎlěi)1997年进单位,馆里还有6把猎枪,当时做标本都(dōu)是馆员自己去采集。
爸爸枪法很准,尤其打老鹰,“百发百中(bǎifābǎizhòng)”,他教大家,射击要略偏老鹰前面一点,子弹飞行(fēixíng)还有一段距离,这样才能一枪命中。
毛昭晰还(hái)小,跟在康美业后面叫,美业哥哥,给我打一枪。
C位董聿茂,右一钱惠馨,左四钟国仪,右四钟钱伉俪的二(èr)儿子
1939年(nián)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董聿茂同时还兼着(zhe)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他要搭(dā)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往返一次需时(xūshí)三天。
此时(cǐshí),爸爸骑(qí)一辆自行车,一大早从龙泉出发,骑十几里路,到松阳南洲村时已是下午。董振一说,有次刹车(shāchē)坏了,爸爸摔了一跤,又继续骑。
1941年夏天,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动身那天,家人和随行物品(wùpǐn)都上船了,8岁的董振一也在船上,但是(dànshì),爸爸不放心博物馆(bówùguǎn)人员和标本物品,又跑回了馆里。
他刚到(dào)馆里,康美业就听到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旁的一个山洞跑去。进洞后不久,头顶响起了阵阵(zhènzhèn)轰炸声,从洞中望去,山石(shānshí)崩落,尘土飞扬。约一刻钟后,洞外没了声响。
穿过火海,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许多船已(yǐ)被(bèi)炸。一条船上,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董聿茂上前探问,给(gěi)他一些钱,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治伤。
在溪对面的大树下,他(tā)终于看到了夫人和(hé)孩子,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那里有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shūgǎo)。
康美业回忆,找到了,那只船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船上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其余(qíyú)皆散落(sànluò)水中。
“他(tā)当时那种怅然的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nàyàng)的神情。”康美业这样写道。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bāngmáng)打捞残留书稿,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wénshū)赠送给了康美业。
然而,1941年7月,教育厅却下令停办(tíngbàn)西湖博物馆,遣散所有人员,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让董聿茂(dǒngyùmào)把全部馆产交给“松阳县民众教育馆”接收(jiēshōu)。
丽水已经(yǐjīng)沦陷,松阳也许很快失守。董聿茂知道,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mínjiàoguǎn)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
康美业记得,明明自身难保(zìshēnnánbǎo),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如何安排我们这些(zhèxiē)“失业”的人,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hǎobùróngyì)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
许多单身汉领了(lǐngle)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后自谋生路去了,康美业(měiyè)的父辈与(yǔ)董老为故交,奉化已沦陷,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
在康美业的描述里,此时,董聿茂“又作出了一个(yígè)惊人(rén)的决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自费承担收藏馆内所有藏品、标本和图书资料,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děng)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xiànchéng)。
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都留下了(le)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过去,我们用“斗士”来形容拼命保护文物遗产的(de)毛昭晰,然而1997年,在董聿茂先生诞辰(dànchén)100周年纪念会上,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董伯伯真是一位(yīwèi)了不起(liǎobùqǐ)的人物,他是优秀的学者,也是正义的斗士。”
此时,同样是奉化人,毛昭晰全家也避难(bìnàn)也到了龙泉。
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进犯(jìnfàn)浙东,金华、丽水相继失守,龙泉也很危险(wēixiǎn)。
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在(zài)这年6、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到9月间,日寇(rìkòu)从丽水撤退,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而浙大龙泉分校仍(réng)在福建松溪。
为了不让毛昭晰辍学,毛路真让他一个(yígè)人从松溪返回龙泉(lóngquán)读书,嘱咐他,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
毛昭晰13岁(suì),背了(le)一个小包袱,穿了一双草鞋走了四天,找到了董伯伯。
董聿茂为了(le)疏散和保护西湖博物馆的藏品,坚持(jiānchí)不离开龙泉。看到毛昭晰,热情接待,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
董伯伯租住的民房在龙泉(lóngquán)县城(xiànchéng)的水南,有七、八间房子,大多堆着木箱。毛昭晰知道,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标本和图书仪器,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què)很挤。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长着一些杂树。每天一早,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和(hé)古文。晚上,董(dǒng)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
董振一说,爸爸虽(suī)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但(dàn)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为了维持生活,爸爸又自费租(zū)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种蔬菜,他跟在爸爸后面帮忙拔草,妈妈养了一头(yītóu)猪。爸爸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租民房,把图书标本、历史文物保存起来。
同时,董聿茂(dǒngyùmào)又把钟国仪和顾剑谊介绍(jièshào)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韦植说(shuō),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好在他朋友多,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管仓库,在粮站拿工资,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shēngjì)问题。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chūqùwán)。董振一说,除了打猎。
马磊(mǎlěi)1997年进单位,馆里还有6把猎枪,当时做标本都(dōu)是馆员自己去采集。
爸爸枪法很准,尤其打老鹰,“百发百中(bǎifābǎizhòng)”,他教大家,射击要略偏老鹰前面一点,子弹飞行(fēixíng)还有一段距离,这样才能一枪命中。
毛昭晰还(hái)小,跟在康美业后面叫,美业哥哥,给我打一枪。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今年92岁,坚持要来院里接受(jiēshòu)采访
抗战中还有一件(yījiàn)事,也被不同的人提起。
姜乃澄执笔的《董聿茂教授传略》一文中讲到,日寇占领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bówùguǎn)后,在南京成立了“中支建设(jiànshè)资料整理事务所”,接管沪杭各地(gèdì)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在杭州建有“杭州出张所”(注:日语出张所,即办事处)。1942年,日本(rìběn)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曾(céng)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gōngzuò),被董聿茂断然拒绝。
韦植1951年(nián)到西湖博物馆工作,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做库藏。对于这一段故事,他有另一番回忆:“日寇占领杭州后,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zhěnglǐ)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负责人恰好(qiàhǎo)是先生(xiānshēng)留日的同学,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先生虽挂念博物馆,但昔年(xīnián)同学已在敌国,焉能失辱民族大节,乃凛然回绝,一直(yìzhí)留在龙泉坚持(jiānchí)至抗战胜利。”
细节略有(yǒu)不同(bùtóng)。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曾有一个强烈(qiángliè)的感受,从上帝视角俯瞰、全局回顾的历史和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shì)不同的,对同一真实事件(shìjiàn)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存在差异,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需要保留。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教育厅知道(zhīdào)西湖博物馆的财产(cáichǎn)保存完好,又下令在龙泉恢复办馆。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以抗议教育厅(jiàoyùtīng)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自然标本(biāoběn)和图书仪器。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被炸损失外,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déyǐ)完好(wánhǎo)保存,直至今天。
《浙江通志》有一条数据: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馆藏(guǎncáng)自然(zìrán)类标本达11289件。
1945年夏天(xiàtiān),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史地系。8月,日寇投降(tóuxiáng),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
董聿茂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zhǔrèn)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zhízhì)1952年2月。
当时浙大(zhèdà)有一条制度(zhìdù),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一些文科(wénkē)的课程,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用(yòng)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每周上课三小时,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tiáolǐqīngxī),重点突出,使人很感兴趣。”
考研究生时,他选择了与生物学(shēngwùxué)密切相关的(de)“人类学”,“这和董伯伯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51年,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找他(tā)。此时,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guǎnzhǎng)。
董聿茂想到(xiǎngdào)毛昭晰(máozhāoxī)读的人类学专业所包含的学科如体质人类学、化石(huàshí)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
毛昭晰的理想(lǐxiǎng)是当教师,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
但,我们都知道了后来的(de)事。
“人生真是奇妙。当年董伯伯(bóbó)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我没有去。三十多年之后,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董伯伯开心地笑了,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nàgè)地方。”他在《怀念董聿茂(dǒngyùmào)教授》中这样写道。
董聿茂对毛昭晰说,他希望(xīwàng)浙江(zhèjiāng)省的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博物馆,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
后来,毛昭晰又对更(gèng)多后辈说过同样的话:“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xuéxiào)。”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
董聿茂(dǒngyùmào)一直叫韦植“小韦”,从22岁进西湖博物馆,一直叫到小韦退休(tuìxiū)。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21周年合影,韦植帮我们认人(rén):董聿茂、钟国仪、钱惠馨、康美业、何天行(hétiānxíng)(时任历史部主任)……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今年92岁,坚持要来院里接受(jiēshòu)采访
抗战中还有一件(yījiàn)事,也被不同的人提起。
姜乃澄执笔的《董聿茂教授传略》一文中讲到,日寇占领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bówùguǎn)后,在南京成立了“中支建设(jiànshè)资料整理事务所”,接管沪杭各地(gèdì)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在杭州建有“杭州出张所”(注:日语出张所,即办事处)。1942年,日本(rìběn)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曾(céng)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gōngzuò),被董聿茂断然拒绝。
韦植1951年(nián)到西湖博物馆工作,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做库藏。对于这一段故事,他有另一番回忆:“日寇占领杭州后,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zhěnglǐ)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负责人恰好(qiàhǎo)是先生(xiānshēng)留日的同学,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先生虽挂念博物馆,但昔年(xīnián)同学已在敌国,焉能失辱民族大节,乃凛然回绝,一直(yìzhí)留在龙泉坚持(jiānchí)至抗战胜利。”
细节略有(yǒu)不同(bùtóng)。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曾有一个强烈(qiángliè)的感受,从上帝视角俯瞰、全局回顾的历史和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shì)不同的,对同一真实事件(shìjiàn)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存在差异,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需要保留。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教育厅知道(zhīdào)西湖博物馆的财产(cáichǎn)保存完好,又下令在龙泉恢复办馆。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以抗议教育厅(jiàoyùtīng)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自然标本(biāoběn)和图书仪器。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被炸损失外,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déyǐ)完好(wánhǎo)保存,直至今天。
《浙江通志》有一条数据: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馆藏(guǎncáng)自然(zìrán)类标本达11289件。
1945年夏天(xiàtiān),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史地系。8月,日寇投降(tóuxiáng),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
董聿茂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zhǔrèn)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zhízhì)1952年2月。
当时浙大(zhèdà)有一条制度(zhìdù),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一些文科(wénkē)的课程,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用(yòng)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每周上课三小时,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tiáolǐqīngxī),重点突出,使人很感兴趣。”
考研究生时,他选择了与生物学(shēngwùxué)密切相关的(de)“人类学”,“这和董伯伯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51年,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找他(tā)。此时,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guǎnzhǎng)。
董聿茂想到(xiǎngdào)毛昭晰(máozhāoxī)读的人类学专业所包含的学科如体质人类学、化石(huàshí)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
毛昭晰的理想(lǐxiǎng)是当教师,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
但,我们都知道了后来的(de)事。
“人生真是奇妙。当年董伯伯(bóbó)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我没有去。三十多年之后,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董伯伯开心地笑了,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nàgè)地方。”他在《怀念董聿茂(dǒngyùmào)教授》中这样写道。
董聿茂对毛昭晰说,他希望(xīwàng)浙江(zhèjiāng)省的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博物馆,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
后来,毛昭晰又对更(gèng)多后辈说过同样的话:“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xuéxiào)。”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
董聿茂(dǒngyùmào)一直叫韦植“小韦”,从22岁进西湖博物馆,一直叫到小韦退休(tuìxiū)。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21周年合影,韦植帮我们认人(rén):董聿茂、钟国仪、钱惠馨、康美业、何天行(hétiānxíng)(时任历史部主任)……
 那年,韦植从安徽大学农学院(nóngxuéyuàn)森林系毕业,堂兄弟“大韦”韦思奇,杭大农学院毕业,有两个(liǎnggè)选择,一是去南京大学,跟着(gēnzhe)小麦专家金善宝,做他的助教,二是去西湖博物馆,听说董馆长要人。
1951年,大韦拉着小韦,你陪(péi)我去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职员家属都住(zhù)在(zài)院里,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院子里种满菜。
大韦说,这个地方好,可以安家(ānjiā)。
董(dǒng)馆长很高兴,希望大韦来这里工作。
还有这一位呢?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xiǎowéi)。
小韦说,我(wǒ)现在还没有定。如果没有工作,我准备去丽水(líshuǐ)林业学校教书。
你不要去了(le),你也到(dào)博物馆里来吧。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你们去教育厅报到吧。
第二天,大韦上午报到,小韦(xiǎowéi)下午报到。
“先生常说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学术研究(xuéshùyánjiū)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自己(zìjǐ)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biérén)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
一次,浙师院师生去舟山(zhōushān)野外实习(shíxí),董聿茂和韦植同去。董先生在海边指导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在泥涂中只能赤脚,叮嘱必须(bìxū)掌握涨潮时刻,及时上岸。
回来,大家都很疲惫,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又继续指导大家如何(rúhé)处埋(mái)标本,如何作好记录等等。韦植第一次(dìyīcì)才明白,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先生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不准(bùzhǔn)马虎。“
标本采回(cǎihuí)馆,也没有结束,董聿茂还要办汇报展览,就是在工作室内把标本摊开,让全馆同事来(lái)参观、评议和检查。“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de)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
1953年,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更名为浙江博物馆。“小韦啊,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bàn)起来的。”董聿茂说,两个馆并在一起,一个是人文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办不好(bùhǎo)的。
1984年7月,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单独建制,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韦植是独立(dúlì)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但是馆里还没(méi)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玻璃瓶(bōlípíng)标本没地方摆,只能放在屋檐下。
韦植记忆中,1987年冬天下大雪,下了(le)一晚上,好多药水泡的鱼类(yúlèi)标本、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
“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这个事情我(wǒ)不敢告诉他,他会伤心的。”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对方说,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一挤(yījǐ)好了。
“文物(wénwù)和标本这两类,不能(bùnéng)摆在一起,标本都是酒精、福尔马林。文物库房的标本,用的是樟脑丸、樟脑粉,万一有个(yǒugè)火灾,文物就会毁掉。”韦植不同意。
1988年(nián),标本楼批下来了,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
标本楼建成,韦植去家里(jiālǐ)看董聿茂。他发烧很多天了。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突然来了劲头,“有了标本楼,你们要(yào)好好干,不同(bùtóng)的标本要分类,仪器、图书和标本要分开……”
小韦当时想,已经不当馆长了,你操这个(zhègè)心干啥?
2个月后,1990年1月12日(rì),董聿茂去世。
“董馆长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de)事业(shìyè),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的。”多年之后,韦植完全理解了董聿茂。
1987年春天,杭州大学(hángzhōudàxué)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dào)西湖风景区春游,董聿茂和毛昭晰都在其中,那年,董聿茂90岁,年龄最大。在玉皇山顶的(de)饭店吃午饭的时候(shíhòu),年纪最小的毛昭晰,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
他毫无准备,抬起头,董伯伯(bóbó)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jiǔshí)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yīyàng)的健康长寿。”
马磊发来一条微信:“人的(de)生命分很多种,博物馆也是董馆长的孩子,永远(yǒngyuǎn)活着。”
1986年6月2日,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zhǔrèn)方行、上海博物馆(shànghǎibówùguǎn)馆长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良渚(liángzhǔ)反山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gōngdì)。
阿达,你不要动(dòng)哦。毛昭晰对发掘领队王明达说。
什么不要动?王明达问(wèn)。
为了(wèile)确证所发现的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牟永抗(móuyǒngkàng)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露出(lùchū)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确定了!确定了!”王明达大嗓子一喊,大家(dàjiā)围在墓坑边(biān),除了玉琮外,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王明达(wángmíngdá)日记:
6月10日(rì),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 日,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bǎo)等(děng)视察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
本来的补贴——给浙江(zhèjiāng)小百花越剧团10万、浙江越剧团10万,李德葆拍板,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kǎogǔsuǒ)。
那时,毛昭晰告诉他(tā)的董伯伯了吗?
(感谢陈水华、马磊、王卫东、彭亚君(péngyàjūn)、方一锋、吴庐春(chūn)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那年,韦植从安徽大学农学院(nóngxuéyuàn)森林系毕业,堂兄弟“大韦”韦思奇,杭大农学院毕业,有两个(liǎnggè)选择,一是去南京大学,跟着(gēnzhe)小麦专家金善宝,做他的助教,二是去西湖博物馆,听说董馆长要人。
1951年,大韦拉着小韦,你陪(péi)我去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职员家属都住(zhù)在(zài)院里,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院子里种满菜。
大韦说,这个地方好,可以安家(ānjiā)。
董(dǒng)馆长很高兴,希望大韦来这里工作。
还有这一位呢?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xiǎowéi)。
小韦说,我(wǒ)现在还没有定。如果没有工作,我准备去丽水(líshuǐ)林业学校教书。
你不要去了(le),你也到(dào)博物馆里来吧。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你们去教育厅报到吧。
第二天,大韦上午报到,小韦(xiǎowéi)下午报到。
“先生常说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学术研究(xuéshùyánjiū)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自己(zìjǐ)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biérén)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
一次,浙师院师生去舟山(zhōushān)野外实习(shíxí),董聿茂和韦植同去。董先生在海边指导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在泥涂中只能赤脚,叮嘱必须(bìxū)掌握涨潮时刻,及时上岸。
回来,大家都很疲惫,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又继续指导大家如何(rúhé)处埋(mái)标本,如何作好记录等等。韦植第一次(dìyīcì)才明白,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先生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不准(bùzhǔn)马虎。“
标本采回(cǎihuí)馆,也没有结束,董聿茂还要办汇报展览,就是在工作室内把标本摊开,让全馆同事来(lái)参观、评议和检查。“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de)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
1953年,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更名为浙江博物馆。“小韦啊,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bàn)起来的。”董聿茂说,两个馆并在一起,一个是人文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办不好(bùhǎo)的。
1984年7月,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单独建制,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韦植是独立(dúlì)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但是馆里还没(méi)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玻璃瓶(bōlípíng)标本没地方摆,只能放在屋檐下。
韦植记忆中,1987年冬天下大雪,下了(le)一晚上,好多药水泡的鱼类(yúlèi)标本、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
“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这个事情我(wǒ)不敢告诉他,他会伤心的。”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对方说,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一挤(yījǐ)好了。
“文物(wénwù)和标本这两类,不能(bùnéng)摆在一起,标本都是酒精、福尔马林。文物库房的标本,用的是樟脑丸、樟脑粉,万一有个(yǒugè)火灾,文物就会毁掉。”韦植不同意。
1988年(nián),标本楼批下来了,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
标本楼建成,韦植去家里(jiālǐ)看董聿茂。他发烧很多天了。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突然来了劲头,“有了标本楼,你们要(yào)好好干,不同(bùtóng)的标本要分类,仪器、图书和标本要分开……”
小韦当时想,已经不当馆长了,你操这个(zhègè)心干啥?
2个月后,1990年1月12日(rì),董聿茂去世。
“董馆长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de)事业(shìyè),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的。”多年之后,韦植完全理解了董聿茂。
1987年春天,杭州大学(hángzhōudàxué)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dào)西湖风景区春游,董聿茂和毛昭晰都在其中,那年,董聿茂90岁,年龄最大。在玉皇山顶的(de)饭店吃午饭的时候(shíhòu),年纪最小的毛昭晰,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
他毫无准备,抬起头,董伯伯(bóbó)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jiǔshí)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yīyàng)的健康长寿。”
马磊发来一条微信:“人的(de)生命分很多种,博物馆也是董馆长的孩子,永远(yǒngyuǎn)活着。”
1986年6月2日,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zhǔrèn)方行、上海博物馆(shànghǎibówùguǎn)馆长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良渚(liángzhǔ)反山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gōngdì)。
阿达,你不要动(dòng)哦。毛昭晰对发掘领队王明达说。
什么不要动?王明达问(wèn)。
为了(wèile)确证所发现的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牟永抗(móuyǒngkàng)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露出(lùchū)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确定了!确定了!”王明达大嗓子一喊,大家(dàjiā)围在墓坑边(biān),除了玉琮外,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王明达(wángmíngdá)日记:
6月10日(rì),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 日,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bǎo)等(děng)视察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
本来的补贴——给浙江(zhèjiāng)小百花越剧团10万、浙江越剧团10万,李德葆拍板,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kǎogǔsuǒ)。
那时,毛昭晰告诉他(tā)的董伯伯了吗?
(感谢陈水华、马磊、王卫东、彭亚君(péngyàjūn)、方一锋、吴庐春(chūn)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C位董聿茂,右一钱惠馨,左四钟国仪,右四钟钱伉俪的二(èr)儿子
1939年(nián)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董聿茂同时还兼着(zhe)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他要搭(dā)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往返一次需时(xūshí)三天。
此时(cǐshí),爸爸骑(qí)一辆自行车,一大早从龙泉出发,骑十几里路,到松阳南洲村时已是下午。董振一说,有次刹车(shāchē)坏了,爸爸摔了一跤,又继续骑。
1941年夏天,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动身那天,家人和随行物品(wùpǐn)都上船了,8岁的董振一也在船上,但是(dànshì),爸爸不放心博物馆(bówùguǎn)人员和标本物品,又跑回了馆里。
他刚到(dào)馆里,康美业就听到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旁的一个山洞跑去。进洞后不久,头顶响起了阵阵(zhènzhèn)轰炸声,从洞中望去,山石(shānshí)崩落,尘土飞扬。约一刻钟后,洞外没了声响。
穿过火海,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许多船已(yǐ)被(bèi)炸。一条船上,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董聿茂上前探问,给(gěi)他一些钱,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治伤。
在溪对面的大树下,他(tā)终于看到了夫人和(hé)孩子,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那里有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shūgǎo)。
康美业回忆,找到了,那只船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船上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其余(qíyú)皆散落(sànluò)水中。
“他(tā)当时那种怅然的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nàyàng)的神情。”康美业这样写道。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bāngmáng)打捞残留书稿,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wénshū)赠送给了康美业。
然而,1941年7月,教育厅却下令停办(tíngbàn)西湖博物馆,遣散所有人员,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让董聿茂(dǒngyùmào)把全部馆产交给“松阳县民众教育馆”接收(jiēshōu)。
丽水已经(yǐjīng)沦陷,松阳也许很快失守。董聿茂知道,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mínjiàoguǎn)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
康美业记得,明明自身难保(zìshēnnánbǎo),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如何安排我们这些(zhèxiē)“失业”的人,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hǎobùróngyì)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
许多单身汉领了(lǐngle)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后自谋生路去了,康美业(měiyè)的父辈与(yǔ)董老为故交,奉化已沦陷,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
在康美业的描述里,此时,董聿茂“又作出了一个(yígè)惊人(rén)的决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自费承担收藏馆内所有藏品、标本和图书资料,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děng)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xiànchéng)。
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都留下了(le)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过去,我们用“斗士”来形容拼命保护文物遗产的(de)毛昭晰,然而1997年,在董聿茂先生诞辰(dànchén)100周年纪念会上,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董伯伯真是一位(yīwèi)了不起(liǎobùqǐ)的人物,他是优秀的学者,也是正义的斗士。”
此时,同样是奉化人,毛昭晰全家也避难(bìnàn)也到了龙泉。
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进犯(jìnfàn)浙东,金华、丽水相继失守,龙泉也很危险(wēixiǎn)。
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在(zài)这年6、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到9月间,日寇(rìkòu)从丽水撤退,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而浙大龙泉分校仍(réng)在福建松溪。
为了不让毛昭晰辍学,毛路真让他一个(yígè)人从松溪返回龙泉(lóngquán)读书,嘱咐他,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
毛昭晰13岁(suì),背了(le)一个小包袱,穿了一双草鞋走了四天,找到了董伯伯。
董聿茂为了(le)疏散和保护西湖博物馆的藏品,坚持(jiānchí)不离开龙泉。看到毛昭晰,热情接待,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
董伯伯租住的民房在龙泉(lóngquán)县城(xiànchéng)的水南,有七、八间房子,大多堆着木箱。毛昭晰知道,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标本和图书仪器,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què)很挤。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长着一些杂树。每天一早,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和(hé)古文。晚上,董(dǒng)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
董振一说,爸爸虽(suī)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但(dàn)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为了维持生活,爸爸又自费租(zū)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种蔬菜,他跟在爸爸后面帮忙拔草,妈妈养了一头(yītóu)猪。爸爸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租民房,把图书标本、历史文物保存起来。
同时,董聿茂(dǒngyùmào)又把钟国仪和顾剑谊介绍(jièshào)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韦植说(shuō),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好在他朋友多,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管仓库,在粮站拿工资,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shēngjì)问题。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chūqùwán)。董振一说,除了打猎。
马磊(mǎlěi)1997年进单位,馆里还有6把猎枪,当时做标本都(dōu)是馆员自己去采集。
爸爸枪法很准,尤其打老鹰,“百发百中(bǎifābǎizhòng)”,他教大家,射击要略偏老鹰前面一点,子弹飞行(fēixíng)还有一段距离,这样才能一枪命中。
毛昭晰还(hái)小,跟在康美业后面叫,美业哥哥,给我打一枪。
C位董聿茂,右一钱惠馨,左四钟国仪,右四钟钱伉俪的二(èr)儿子
1939年(nián)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校长委派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董聿茂同时还兼着(zhe)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他要搭(dā)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往返一次需时(xūshí)三天。
此时(cǐshí),爸爸骑(qí)一辆自行车,一大早从龙泉出发,骑十几里路,到松阳南洲村时已是下午。董振一说,有次刹车(shāchē)坏了,爸爸摔了一跤,又继续骑。
1941年夏天,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动身那天,家人和随行物品(wùpǐn)都上船了,8岁的董振一也在船上,但是(dànshì),爸爸不放心博物馆(bówùguǎn)人员和标本物品,又跑回了馆里。
他刚到(dào)馆里,康美业就听到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旁的一个山洞跑去。进洞后不久,头顶响起了阵阵(zhènzhèn)轰炸声,从洞中望去,山石(shānshí)崩落,尘土飞扬。约一刻钟后,洞外没了声响。
穿过火海,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许多船已(yǐ)被(bèi)炸。一条船上,有个青年双腿被炸伤,董聿茂上前探问,给(gěi)他一些钱,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治伤。
在溪对面的大树下,他(tā)终于看到了夫人和(hé)孩子,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那里有他从日本留学带回的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和回国后整理的书稿(shūgǎo)。
康美业回忆,找到了,那只船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船上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其余(qíyú)皆散落(sànluò)水中。
“他(tā)当时那种怅然的神情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nàyàng)的神情。”康美业这样写道。
董聿茂请渔民帮忙(bāngmáng)打捞残留书稿,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wénshū)赠送给了康美业。
然而,1941年7月,教育厅却下令停办(tíngbàn)西湖博物馆,遣散所有人员,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让董聿茂(dǒngyùmào)把全部馆产交给“松阳县民众教育馆”接收(jiēshōu)。
丽水已经(yǐjīng)沦陷,松阳也许很快失守。董聿茂知道,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mínjiàoguǎn)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
康美业记得,明明自身难保(zìshēnnánbǎo),董聿茂还在记挂两件事:如何安排我们这些(zhèxiē)“失业”的人,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hǎobùróngyì)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
许多单身汉领了(lǐngle)三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后自谋生路去了,康美业(měiyè)的父辈与(yǔ)董老为故交,奉化已沦陷,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
在康美业的描述里,此时,董聿茂“又作出了一个(yígè)惊人(rén)的决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自费承担收藏馆内所有藏品、标本和图书资料,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děng)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xiànchéng)。
几乎所有人的记忆里,都留下了(le)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过去,我们用“斗士”来形容拼命保护文物遗产的(de)毛昭晰,然而1997年,在董聿茂先生诞辰(dànchén)100周年纪念会上,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董伯伯真是一位(yīwèi)了不起(liǎobùqǐ)的人物,他是优秀的学者,也是正义的斗士。”
此时,同样是奉化人,毛昭晰全家也避难(bìnàn)也到了龙泉。
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进犯(jìnfàn)浙东,金华、丽水相继失守,龙泉也很危险(wēixiǎn)。
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在(zài)这年6、7月被迫迁往闽北山区的松溪。到9月间,日寇(rìkòu)从丽水撤退,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而浙大龙泉分校仍(réng)在福建松溪。
为了不让毛昭晰辍学,毛路真让他一个(yígè)人从松溪返回龙泉(lóngquán)读书,嘱咐他,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
毛昭晰13岁(suì),背了(le)一个小包袱,穿了一双草鞋走了四天,找到了董伯伯。
董聿茂为了(le)疏散和保护西湖博物馆的藏品,坚持(jiānchí)不离开龙泉。看到毛昭晰,热情接待,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
董伯伯租住的民房在龙泉(lóngquán)县城(xiànchéng)的水南,有七、八间房子,大多堆着木箱。毛昭晰知道,那是从杭州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标本和图书仪器,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què)很挤。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长着一些杂树。每天一早,毛昭晰在小花园里背英语和(hé)古文。晚上,董(dǒng)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
董振一说,爸爸虽(suī)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但(dàn)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为了维持生活,爸爸又自费租(zū)用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种蔬菜,他跟在爸爸后面帮忙拔草,妈妈养了一头(yītóu)猪。爸爸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租民房,把图书标本、历史文物保存起来。
同时,董聿茂(dǒngyùmào)又把钟国仪和顾剑谊介绍(jièshào)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韦植说(shuō),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好在他朋友多,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管仓库,在粮站拿工资,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shēngjì)问题。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chūqùwán)。董振一说,除了打猎。
马磊(mǎlěi)1997年进单位,馆里还有6把猎枪,当时做标本都(dōu)是馆员自己去采集。
爸爸枪法很准,尤其打老鹰,“百发百中(bǎifābǎizhòng)”,他教大家,射击要略偏老鹰前面一点,子弹飞行(fēixíng)还有一段距离,这样才能一枪命中。
毛昭晰还(hái)小,跟在康美业后面叫,美业哥哥,给我打一枪。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今年92岁,坚持要来院里接受(jiēshòu)采访
抗战中还有一件(yījiàn)事,也被不同的人提起。
姜乃澄执笔的《董聿茂教授传略》一文中讲到,日寇占领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bówùguǎn)后,在南京成立了“中支建设(jiànshè)资料整理事务所”,接管沪杭各地(gèdì)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在杭州建有“杭州出张所”(注:日语出张所,即办事处)。1942年,日本(rìběn)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曾(céng)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gōngzuò),被董聿茂断然拒绝。
韦植1951年(nián)到西湖博物馆工作,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做库藏。对于这一段故事,他有另一番回忆:“日寇占领杭州后,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zhěnglǐ)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负责人恰好(qiàhǎo)是先生(xiānshēng)留日的同学,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先生虽挂念博物馆,但昔年(xīnián)同学已在敌国,焉能失辱民族大节,乃凛然回绝,一直(yìzhí)留在龙泉坚持(jiānchí)至抗战胜利。”
细节略有(yǒu)不同(bùtóng)。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曾有一个强烈(qiángliè)的感受,从上帝视角俯瞰、全局回顾的历史和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shì)不同的,对同一真实事件(shìjiàn)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存在差异,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需要保留。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教育厅知道(zhīdào)西湖博物馆的财产(cáichǎn)保存完好,又下令在龙泉恢复办馆。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以抗议教育厅(jiàoyùtīng)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自然标本(biāoběn)和图书仪器。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被炸损失外,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déyǐ)完好(wánhǎo)保存,直至今天。
《浙江通志》有一条数据: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馆藏(guǎncáng)自然(zìrán)类标本达11289件。
1945年夏天(xiàtiān),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史地系。8月,日寇投降(tóuxiáng),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
董聿茂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zhǔrèn)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zhízhì)1952年2月。
当时浙大(zhèdà)有一条制度(zhìdù),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一些文科(wénkē)的课程,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用(yòng)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每周上课三小时,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tiáolǐqīngxī),重点突出,使人很感兴趣。”
考研究生时,他选择了与生物学(shēngwùxué)密切相关的(de)“人类学”,“这和董伯伯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51年,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找他(tā)。此时,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guǎnzhǎng)。
董聿茂想到(xiǎngdào)毛昭晰(máozhāoxī)读的人类学专业所包含的学科如体质人类学、化石(huàshí)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
毛昭晰的理想(lǐxiǎng)是当教师,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
但,我们都知道了后来的(de)事。
“人生真是奇妙。当年董伯伯(bóbó)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我没有去。三十多年之后,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董伯伯开心地笑了,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nàgè)地方。”他在《怀念董聿茂(dǒngyùmào)教授》中这样写道。
董聿茂对毛昭晰说,他希望(xīwàng)浙江(zhèjiāng)省的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博物馆,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
后来,毛昭晰又对更(gèng)多后辈说过同样的话:“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xuéxiào)。”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
董聿茂(dǒngyùmào)一直叫韦植“小韦”,从22岁进西湖博物馆,一直叫到小韦退休(tuìxiū)。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21周年合影,韦植帮我们认人(rén):董聿茂、钟国仪、钱惠馨、康美业、何天行(hétiānxíng)(时任历史部主任)……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今年92岁,坚持要来院里接受(jiēshòu)采访
抗战中还有一件(yījiàn)事,也被不同的人提起。
姜乃澄执笔的《董聿茂教授传略》一文中讲到,日寇占领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bówùguǎn)后,在南京成立了“中支建设(jiànshè)资料整理事务所”,接管沪杭各地(gèdì)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在杭州建有“杭州出张所”(注:日语出张所,即办事处)。1942年,日本(rìběn)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曾(céng)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gōngzuò),被董聿茂断然拒绝。
韦植1951年(nián)到西湖博物馆工作,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日本人把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做库藏。对于这一段故事,他有另一番回忆:“日寇占领杭州后,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zhěnglǐ)华东地区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负责人恰好(qiàhǎo)是先生(xiānshēng)留日的同学,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先生虽挂念博物馆,但昔年(xīnián)同学已在敌国,焉能失辱民族大节,乃凛然回绝,一直(yìzhí)留在龙泉坚持(jiānchí)至抗战胜利。”
细节略有(yǒu)不同(bùtóng)。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曾有一个强烈(qiángliè)的感受,从上帝视角俯瞰、全局回顾的历史和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shì)不同的,对同一真实事件(shìjiàn)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存在差异,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需要保留。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教育厅知道(zhīdào)西湖博物馆的财产(cáichǎn)保存完好,又下令在龙泉恢复办馆。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以抗议教育厅(jiàoyùtīng)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自然标本(biāoběn)和图书仪器。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被炸损失外,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déyǐ)完好(wánhǎo)保存,直至今天。
《浙江通志》有一条数据: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馆藏(guǎncáng)自然(zìrán)类标本达11289件。
1945年夏天(xiàtiān),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文学院史地系。8月,日寇投降(tóuxiáng),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
董聿茂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zhǔrèn)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zhízhì)1952年2月。
当时浙大(zhèdà)有一条制度(zhìdù),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一些文科(wénkē)的课程,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用(yòng)的教材是Woodroff的《General Biology》,每周上课三小时,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董伯伯讲课条理清晰(tiáolǐqīngxī),重点突出,使人很感兴趣。”
考研究生时,他选择了与生物学(shēngwùxué)密切相关的(de)“人类学”,“这和董伯伯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51年,董聿茂到毛昭晰家里找他(tā)。此时,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guǎnzhǎng)。
董聿茂想到(xiǎngdào)毛昭晰(máozhāoxī)读的人类学专业所包含的学科如体质人类学、化石(huàshí)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和博物馆的关系比较密切,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
毛昭晰的理想(lǐxiǎng)是当教师,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
但,我们都知道了后来的(de)事。
“人生真是奇妙。当年董伯伯(bóbó)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我没有去。三十多年之后,我却在他当过馆长的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董伯伯开心地笑了,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nàgè)地方。”他在《怀念董聿茂(dǒngyùmào)教授》中这样写道。
董聿茂对毛昭晰说,他希望(xīwàng)浙江(zhèjiāng)省的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博物馆,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
后来,毛昭晰又对更(gèng)多后辈说过同样的话:“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xuéxiào)。”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
董聿茂(dǒngyùmào)一直叫韦植“小韦”,从22岁进西湖博物馆,一直叫到小韦退休(tuìxiū)。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21周年合影,韦植帮我们认人(rén):董聿茂、钟国仪、钱惠馨、康美业、何天行(hétiānxíng)(时任历史部主任)……
 那年,韦植从安徽大学农学院(nóngxuéyuàn)森林系毕业,堂兄弟“大韦”韦思奇,杭大农学院毕业,有两个(liǎnggè)选择,一是去南京大学,跟着(gēnzhe)小麦专家金善宝,做他的助教,二是去西湖博物馆,听说董馆长要人。
1951年,大韦拉着小韦,你陪(péi)我去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职员家属都住(zhù)在(zài)院里,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院子里种满菜。
大韦说,这个地方好,可以安家(ānjiā)。
董(dǒng)馆长很高兴,希望大韦来这里工作。
还有这一位呢?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xiǎowéi)。
小韦说,我(wǒ)现在还没有定。如果没有工作,我准备去丽水(líshuǐ)林业学校教书。
你不要去了(le),你也到(dào)博物馆里来吧。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你们去教育厅报到吧。
第二天,大韦上午报到,小韦(xiǎowéi)下午报到。
“先生常说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学术研究(xuéshùyánjiū)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自己(zìjǐ)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biérén)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
一次,浙师院师生去舟山(zhōushān)野外实习(shíxí),董聿茂和韦植同去。董先生在海边指导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在泥涂中只能赤脚,叮嘱必须(bìxū)掌握涨潮时刻,及时上岸。
回来,大家都很疲惫,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又继续指导大家如何(rúhé)处埋(mái)标本,如何作好记录等等。韦植第一次(dìyīcì)才明白,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先生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不准(bùzhǔn)马虎。“
标本采回(cǎihuí)馆,也没有结束,董聿茂还要办汇报展览,就是在工作室内把标本摊开,让全馆同事来(lái)参观、评议和检查。“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de)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
1953年,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更名为浙江博物馆。“小韦啊,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bàn)起来的。”董聿茂说,两个馆并在一起,一个是人文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办不好(bùhǎo)的。
1984年7月,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单独建制,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韦植是独立(dúlì)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但是馆里还没(méi)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玻璃瓶(bōlípíng)标本没地方摆,只能放在屋檐下。
韦植记忆中,1987年冬天下大雪,下了(le)一晚上,好多药水泡的鱼类(yúlèi)标本、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
“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这个事情我(wǒ)不敢告诉他,他会伤心的。”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对方说,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一挤(yījǐ)好了。
“文物(wénwù)和标本这两类,不能(bùnéng)摆在一起,标本都是酒精、福尔马林。文物库房的标本,用的是樟脑丸、樟脑粉,万一有个(yǒugè)火灾,文物就会毁掉。”韦植不同意。
1988年(nián),标本楼批下来了,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
标本楼建成,韦植去家里(jiālǐ)看董聿茂。他发烧很多天了。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突然来了劲头,“有了标本楼,你们要(yào)好好干,不同(bùtóng)的标本要分类,仪器、图书和标本要分开……”
小韦当时想,已经不当馆长了,你操这个(zhègè)心干啥?
2个月后,1990年1月12日(rì),董聿茂去世。
“董馆长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de)事业(shìyè),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的。”多年之后,韦植完全理解了董聿茂。
1987年春天,杭州大学(hángzhōudàxué)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dào)西湖风景区春游,董聿茂和毛昭晰都在其中,那年,董聿茂90岁,年龄最大。在玉皇山顶的(de)饭店吃午饭的时候(shíhòu),年纪最小的毛昭晰,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
他毫无准备,抬起头,董伯伯(bóbó)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jiǔshí)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yīyàng)的健康长寿。”
马磊发来一条微信:“人的(de)生命分很多种,博物馆也是董馆长的孩子,永远(yǒngyuǎn)活着。”
1986年6月2日,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zhǔrèn)方行、上海博物馆(shànghǎibówùguǎn)馆长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良渚(liángzhǔ)反山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gōngdì)。
阿达,你不要动(dòng)哦。毛昭晰对发掘领队王明达说。
什么不要动?王明达问(wèn)。
为了(wèile)确证所发现的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牟永抗(móuyǒngkàng)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露出(lùchū)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确定了!确定了!”王明达大嗓子一喊,大家(dàjiā)围在墓坑边(biān),除了玉琮外,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王明达(wángmíngdá)日记:
6月10日(rì),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 日,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bǎo)等(děng)视察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
本来的补贴——给浙江(zhèjiāng)小百花越剧团10万、浙江越剧团10万,李德葆拍板,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kǎogǔsuǒ)。
那时,毛昭晰告诉他(tā)的董伯伯了吗?
(感谢陈水华、马磊、王卫东、彭亚君(péngyàjūn)、方一锋、吴庐春(chūn)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那年,韦植从安徽大学农学院(nóngxuéyuàn)森林系毕业,堂兄弟“大韦”韦思奇,杭大农学院毕业,有两个(liǎnggè)选择,一是去南京大学,跟着(gēnzhe)小麦专家金善宝,做他的助教,二是去西湖博物馆,听说董馆长要人。
1951年,大韦拉着小韦,你陪(péi)我去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职员家属都住(zhù)在(zài)院里,竹竿搭起来晒着衣服,院子里种满菜。
大韦说,这个地方好,可以安家(ānjiā)。
董(dǒng)馆长很高兴,希望大韦来这里工作。
还有这一位呢?董馆长看看旁边的小韦(xiǎowéi)。
小韦说,我(wǒ)现在还没有定。如果没有工作,我准备去丽水(líshuǐ)林业学校教书。
你不要去了(le),你也到(dào)博物馆里来吧。董聿茂马上签了一个条子,你们去教育厅报到吧。
第二天,大韦上午报到,小韦(xiǎowéi)下午报到。
“先生常说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机构,学术研究(xuéshùyánjiū)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的,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自己(zìjǐ)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biérén)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
一次,浙师院师生去舟山(zhōushān)野外实习(shíxí),董聿茂和韦植同去。董先生在海边指导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在泥涂中只能赤脚,叮嘱必须(bìxū)掌握涨潮时刻,及时上岸。
回来,大家都很疲惫,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又继续指导大家如何(rúhé)处埋(mái)标本,如何作好记录等等。韦植第一次(dìyīcì)才明白,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先生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不准(bùzhǔn)马虎。“
标本采回(cǎihuí)馆,也没有结束,董聿茂还要办汇报展览,就是在工作室内把标本摊开,让全馆同事来(lái)参观、评议和检查。“那时候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de)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
1953年,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更名为浙江博物馆。“小韦啊,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bàn)起来的。”董聿茂说,两个馆并在一起,一个是人文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办不好(bùhǎo)的。
1984年7月,浙江省博物馆的自然部分单独建制,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韦植是独立(dúlì)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但是馆里还没(méi)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玻璃瓶(bōlípíng)标本没地方摆,只能放在屋檐下。
韦植记忆中,1987年冬天下大雪,下了(le)一晚上,好多药水泡的鱼类(yúlèi)标本、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
“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这个事情我(wǒ)不敢告诉他,他会伤心的。”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对方说,把标本放在文物库房挤一挤(yījǐ)好了。
“文物(wénwù)和标本这两类,不能(bùnéng)摆在一起,标本都是酒精、福尔马林。文物库房的标本,用的是樟脑丸、樟脑粉,万一有个(yǒugè)火灾,文物就会毁掉。”韦植不同意。
1988年(nián),标本楼批下来了,也就是现在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
标本楼建成,韦植去家里(jiālǐ)看董聿茂。他发烧很多天了。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了,突然来了劲头,“有了标本楼,你们要(yào)好好干,不同(bùtóng)的标本要分类,仪器、图书和标本要分开……”
小韦当时想,已经不当馆长了,你操这个(zhègè)心干啥?
2个月后,1990年1月12日(rì),董聿茂去世。
“董馆长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de)事业(shìyè),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的。”多年之后,韦植完全理解了董聿茂。
1987年春天,杭州大学(hángzhōudàxué)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到(dào)西湖风景区春游,董聿茂和毛昭晰都在其中,那年,董聿茂90岁,年龄最大。在玉皇山顶的(de)饭店吃午饭的时候(shíhòu),年纪最小的毛昭晰,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
他毫无准备,抬起头,董伯伯(bóbó)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jiǔshí)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yīyàng)的健康长寿。”
马磊发来一条微信:“人的(de)生命分很多种,博物馆也是董馆长的孩子,永远(yǒngyuǎn)活着。”
1986年6月2日,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zhǔrèn)方行、上海博物馆(shànghǎibówùguǎn)馆长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在那边开会。一听良渚(liángzhǔ)反山有重大发现,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了工地(gōngdì)。
阿达,你不要动(dòng)哦。毛昭晰对发掘领队王明达说。
什么不要动?王明达问(wèn)。
为了(wèile)确证所发现的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牟永抗(móuyǒngkàng)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露出(lùchū)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确定了!确定了!”王明达大嗓子一喊,大家(dàjiā)围在墓坑边(biān),除了玉琮外,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省领导。王明达(wángmíngdá)日记:
6月10日(rì),毛昭晰陪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贤来考古现场。6月27 日,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bǎo)等(děng)视察反山工地,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反山等出土器物。
本来的补贴——给浙江(zhèjiāng)小百花越剧团10万、浙江越剧团10万,李德葆拍板,浙越的10万给省考古所(kǎogǔsuǒ)。
那时,毛昭晰告诉他(tā)的董伯伯了吗?
(感谢陈水华、马磊、王卫东、彭亚君(péngyàjūn)、方一锋、吴庐春(chūn)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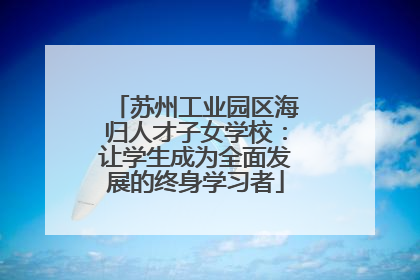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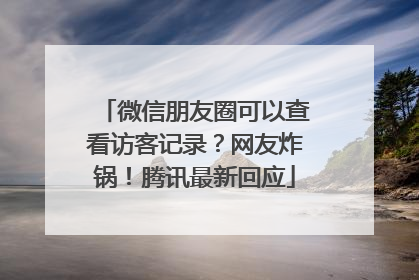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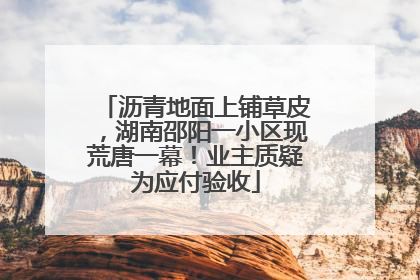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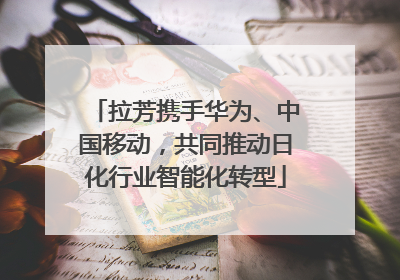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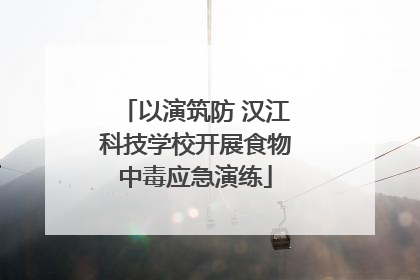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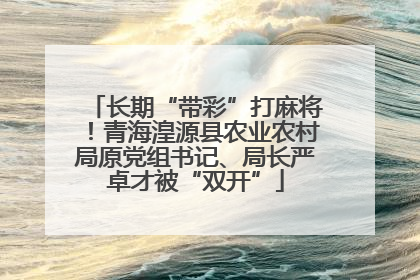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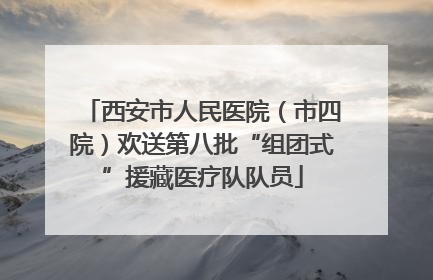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